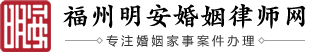《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当代的婚姻家庭立法在理念和技术上的突破性发展,婚姻家庭法由此实现了从政治法向市民法的转变。然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继承具有局限性,其回应社会生活的能力仍有待加强。对此,吉林大学法学院李拥军教授在《民法典时代的婚姻家庭立法的突破与局限》一文中,指明法典化时代的婚姻家庭法仍然需要通过不断修正的方式来弥合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仍然需要借助司法解释和案例制度来弥补自身的局限,借助习惯、伦理等社会规范来解决纠纷。
(一)新婚姻家庭法并非完全具有了私法的属性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采取的是民法典之外的单独立法模式,借鉴的是苏联“不承认任何私法”的立法经验。在这种理念下,婚姻法具有了公法的性质。虽然后经两次修订,但整个立法基调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婚姻家庭法逐渐褪去政治性而回归世俗性的进程的加快,对其回归民法属性的呼声也逐渐增强。而《民法典》的出台意味着,婚姻家庭法正式回归于民法。但其仅是形式上回归了民法体系,并不能说明其完全具有了私法的属性。其一,传统公私法的划分存在缺陷,因任何一种法都出自于国家,具有公共性和强行性。随着私法公法化之趋势,现代民法的私法性亦并不纯粹,新婚姻家庭法亦并不当然具有私法的属性。其二,家庭领域的人身性和伦理性决定了婚姻家庭法必然要超越私法的属性,需要强行性规范来维护社会公平和家庭稳定。其三,权利本位是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需坚持的基本原则,不为私法独有。故即使《民法典》在婚姻家庭领域作了大量的权利方面的规定,亦不能就此简单地将其认定为私法。
(二)新婚姻家庭法完成了从政治法到市民法的转变才是关键
与其在公私法的框架内来观察当下的婚姻家庭法,不如在国家——社会的视角下对其加以审视。单独立法模式下的《婚姻法》是为了配合国家改造社会而产生的,而回归于《民法典》的婚姻家庭法须实现从政治法到市民法的变迁,这已体现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具体规定之中。譬如,取消原《婚姻法》中计划生育的内容,意味着不再通过这一形式对自然人的生育权进行限制,生育权重归于家庭;变更原《婚姻法》中“患有医学上的严重疾病是无效婚姻的事由”为“可撤销婚姻的事由”,表明婚姻效力的决定权被更多地赋予了当事人,更符合意思自治的原则。新婚姻家庭法应突破以婚姻为主线的制度设计模式,切实体现其身份法的特征,恢复其家庭法、亲属法、身份法的原貌。相较于纠结婚姻家庭法的公私属性,在上述方面作出实际的努力和回应才是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立法之重心。
(一)新婚姻家庭法继承的力度和规模仍有不足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国家的传统与文化。家文化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故面向中国建设法治就不能无视“家”的存在。婚姻家庭法作为直接调整家庭关系的法律应当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有所回应。特别是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在凝练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构建中国法治话语权的语境下,《民法典》更应该对此有所作为。
但从《民法典》的修订来看,婚姻家庭编对传统的承继和回应还不够,仅局限于“家风家德”等倡导性条款;“夫妻忠实”、“敬老爱幼”等传统观念的法律化以及“抚养、赡养、扶养”等条款的沿用。虽然这些规定可以被看成是对中国传统的“慈”“孝”“悌”观念在法律上的承继,但对于一些现实问题仍未能结合传统伦理与文化进行补充完善。譬如,《民法典》中对亲属问题的规定过于简单:一方面,缺失对亲等的规定,无法科学地反映亲属关系的远近;其二,缺失对姻亲范围的具体规定,使得人们在处理婚姻管理、亲属回避等事项上无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新婚姻家庭法拓展的范围和内容存有空间
其一,关于通婚禁止的问题。《民法典》所沿袭的“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这一规定只考虑了血缘因素。但从中国传统伦理上讲,对于宗亲属来说,无论是代际间还是同代间,即使血缘关系比较远,通常也是不允许通婚的;对于较近的代际间的姻亲,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允许通婚。立法者在就通婚作禁止性规定时,忽略了中国传统伦理上代际身份、亲属类别等限制。其二,关于婚约彩礼的问题。婚约和彩礼是流行于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重要的婚嫁习俗。从法律的角度看,彩礼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婚姻契约缔结中的订金或保证金的作用,具有严肃婚姻观念的功能。特别是在当下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广大农村地区,彩礼现象更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但《民法典》未能对此作出具体的回应实属遗憾。其三,关于事实婚姻问题。《民法典》沿用单一的登记婚形式,未能回应传统仪式婚的价值,或将在某些情况下损害妇女、未成年子女等弱者的利益。毕竟事实婚姻所牵扯到的法律问题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不承认其效力或将其认定为“非法同居关系”就能解决的。
(一)新婚姻家庭法仍需通过断修正的方式来弥合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值得肯定的是,《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将原有的《收养法》编入其中以及对原有《婚姻法》的很多地方作了实质性的修改,适应了当下中国婚姻家庭领域所发生的实际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法律调整社会的能力,法律的系统化程度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然而,婚姻家庭编对于当下中国多元化的婚姻形态和家庭结构的现实回应确有不足:其一,《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同居关系未作规定。在同居现象日益普遍化的当下,对于同居关系不予规制,一旦发生损害,处于同居关系的女方及其子女、以及同居老年丧偶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护。其二,《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通过人工生殖技术生育子女的现象未作回应。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们权利意识的提升,此类现象引发的法律问题频发,最为典型的是人工授精和代孕问题。虽然最高院有相关指导案例,但范围局限,不足以涵盖更多案型。其三,《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于亲子关系仅作了基础性或一般性规定(第1073条),难以适应纠纷的复杂多变。其四,《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对收养的条件虽然有所放宽,但依然过于严格。
《民法典》未能全面回应社会生活的问题,除了立法者自身的原因外,还与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有关。法典自身的稳定性的内在需求会导致其对社会生活的回应能力的降低。
(二)新婚姻家庭法仍需借助司法解释和案例制度来弥补自身的局限
诚然,《民法典》的编纂多立足于原有的《婚姻法》和《收养法》文本,未能对原有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所确立的规则予以很好的整合和吸收。但即使其很好地做到了这点,它仍然需要新的解释和案例。一方面,在实践中,法典必须借助司法解释才能发挥其作用。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可以弥补法律文本在微观方面的不足,同时,成文法规则自身表述的简练化特点也决定了,如果不对某些条文进行具体的解释,将无法保证其在实践中得到准确的应用。另一方面,规范文本的表达局限可以通过案例指导制度来克服。法律文本和司法解释都存在着语言表达上的局限,加之婚姻家庭领域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因素,使得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被赋予更多的自由裁量权,为实践创造规则提供了条件。这种由实践创生规则的形式集中表现在案例指导制度之中。虽然我国原则上不承认判例的法源地位,但来源于司法实践的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等经过最高司法机关的发布以后,事实上发挥着示范作用和约束力。故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中的“裁判理由”和典型案例中的“典型意义”实际上便发挥着裁判规则的作用。
(三)新婚姻家庭法仍需借助习惯、伦理等社会规范来解决纠纷
在当下的中国,民间的习惯性规则绝大部分都存留在婚姻家庭领域,而家事纠纷的内部性、可调解性的特点使这些伦理习惯有了发挥作用的空间。由此说来,即使在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法律也不可能单独依靠正式文本来调整家庭关系,同样还需要借助民间社会规范来辅助纠纷的解决。
婚姻家庭法的回归是民法体系不断完善的结果。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有对传统的承继和对现实的回应,但由于受到法典自身的局限性、婚姻家庭关系的特点以及本次民法典编篡技术上的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新婚姻家庭法仍有待补充完善。尤其在司法判例和单行法的冲击和解构下,解决婚姻家庭法律与现实的冲突要更多地在促进立法与传统、民情的有机融合上下功夫。婚姻家庭法的系统化运动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法律与实践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