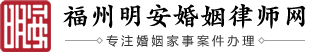凤凰网读书 微信公号
婚内出轨、婚内包养,不仅是茶余饭后的巷尾谈资,也是一呼百应的公共议题,这从多部热播电视剧的人物设定与观众反馈中可见一斑。
事实上,虽人人对“出轨男”表现得嫉恶如仇,但“婚外恋”至今仍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因为它在具有天然的八卦性和隐私性的同时,也与道德、欲望、权力、面子等严肃的命题息息相关。
学者肖索未在北大读博期间,曾对几位有婚内包养关系的男性进行深度访谈,他们如何理解婚姻?如何解释自己的婚外亲密关系?又如何为自己不符合主流道德的“出轨”行为辩护?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或许有助于厘清个体与家庭、亲密关系与婚姻制度之间的张力,以及隐含于其中的性别规则和阶层符码。
50岁的宁波男人老王感叹婚姻不幸,用他的话说“结婚廿多年,吵了十多年”。
老王和妻子在1980年代初结婚。妻子方荔比他小两岁,也是宁波本地人。婚姻最初几年两人都在工厂上班,挣得不多,但日子过得还不错。1990年代初两人工作的厂子的效益越来越差,方荔经过熟人介绍换到一家事业单位当会计,工作稳定但收入有限。她希望自己“主内”,管好家里和孩子,而老王能够“主外”,多赚钱,改善家庭经济条件。
在方荔眼中,老王惰性很大,不管不行。在她的督促下,老王考了驾照,开起了出租车。几年后,在方荔亲戚的帮助下,老王调到一个国营单位给领导开车。家里经济条件好了一些,但与方荔姐妹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姐夫妹夫前几年分别下海,生意越做越好。方荔希望老王多跟他们学习,但老王却不爱去她娘家,“每次去总感觉低人一头”,经常去了也一言不发,而方荔则觉得老王“不上进”、“不学好”,免不了争吵。
在方荔的敦促下,老王硬着头皮和妻子一起开始读函授大专,中间好几次想放弃,方荔软硬兼施,劝说、鼓励、批评、责备轮番上阵,还帮他完成作业,老王好不容易拿到了学位。有了大专文凭,老王从给领导开车换到了办公室做行政工作,事业编制,收入比之前增加不少。回想这段往事,老王表示“这事(文凭)还真多亏了方荔”。
两人最大的矛盾在老王的“爱好”上。老王三十多岁时迷上打麻将,经常打得三更半夜才回家。老王觉得这是自己“唯一的爱好”,“放松放松,跟朋友聚聚”。方荔则觉得打麻将毁了老王——“工作没心思”、“儿子也不管”;她对此深恶痛绝,希望老王戒掉恶习。一开始,她苦口婆心劝说,收效甚微,之后又采取了反锁房门不让老王进、到打牌的地方去“抓人”等激烈的方式。方荔认为,“因为他是我老公,我才去说他管他。眼看他染上坏习惯,随他去,那就不是自己家里人了”。但老王并不领情,两人争吵不断,越吵越凶。
在方荔看来,和老王的婚姻虽不完美,但还是“好”的。夫妻之间有深厚的感情。“以前我们俩每天晚上聊天聊到两三点钟,”她说,“我们也吵架,夫妻吵架很正常。我们没有本质性的问题,吵架无非是两件事:他打麻将、儿子的教育。他把时间都浪费在麻将牌上,我希望他多和儿子处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这个家。”
老王则认为这种家庭生活状态已经让他非常不满。他觉得妻子烦、唠叨、脾气差,成天拿他跟连襟比,不给他面子,搞得家里气氛很压抑,让他根本不想待。跟比他小二十岁的小梅在一起后,老王觉得找到了一些家的温馨和愉悦,因为小梅觉得他是个“很好的男人”,从不要求他做什么。老王带着过来人的口气对我说:“我跟你说,实际上这个社会真的在进步,因为人总想往好的过,对吧?就不喜欢过原来那种窝囊的日子。”我问他窝囊指什么,老王说:
窝囊是指家庭问题,两夫妻总是互相生气。因为像我的父辈,就没有这种观念,像我老爸和我老妈,关系很紧张,到最终,当然我们做子女的说不出这个口,你们离婚吧。但实际上他们是该离婚,就是说他们虽然没离婚,但实际上跟离婚差不多,就是表面上是夫妻,实际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都很讨厌了。但是他们没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凑合着过,不是饥寒交迫,不是物质生活的不幸,是感情生活上。
如何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与竞争风险并存以及社会保障不足的状况,是摆在转型社会所有家庭面前的问题。作为工厂职工,老王一家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而这个压力因妻子娘家姐妹的“先富起来”变得真切。如何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如何应对被姐妹们甩下的“相对剥夺”?这是老王家的难题,也是夫妻俩冲突的焦点。
在对1990年代大连家庭的研究中,人类学家Lisa Hoffman发现很多工薪家庭在面临市场压力时,采取被她称为“一家两制”的家庭策略,兼顾“稳定与发展”:丈夫“下海”,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中追求高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而妻子则在安全、稳定和体面的公职岗位上班——这些工作工资低但强度小、不用出差,能兼顾料理家事、照顾家中老小。老王家与此无异,以家庭为单位,老王去市场挣钱,方荔工作稳定以家庭为重心。这样的性别分工将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寄托在老王身上。
方荔“管”老王,正是把家庭视作一个整体。这里既有之前提到的“夫妻一体”的文化预设,“管”意味着把对方当作“自己家里人”,是一种关切和在意,也是一个好妻子的责任。她希望丈夫“上进”,不满足现状,积极进取。这既符合社会对优秀男性的评价,又保持着家庭提升的希望。因此,“管”是作为妻子的方荔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非淘汰者、摆脱“相对剥夺”感的手段。方荔的“管”也起到了实际成效,比如敦促丈夫考驾照、拿文凭,帮助丈夫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老王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对此也了然于心。
然而,这个过程也加剧了家庭整体利益与丈夫个体诉求之间的冲突,往往会以“夫妻争吵”的方式显露出来。在方荔看来,家是“同甘共苦”的共同体,争吵在“夫妻一体”的前提下并不影响夫妻关系,甚至是她敦促丈夫的努力,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经受的阶段性磨难而已。而老王则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权利:他有权有自己的爱好,有权休闲,妻子不应该“管”。与妻子相比,老王更强调家庭生活的状态,期望获得情感愉悦与满足。
作为工薪阶层,他努力挣钱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无望追上亲戚们“先富”的脚步。他希望满足现状,得到妻子的认可、肯定和嘘寒问暖。持续不断的争吵让他感受不到“家的温馨”,反而非常压抑。他所强调的家庭的情感意义,不仅是“同甘共苦”的共同体模式,而且包含了强调个体边界和过程体验的“相处愉快”模式。婚姻中,如果没有后者,则被他视为“窝囊”的、凑合过日子的生活,是“进步了的社会”需要摆脱的婚姻状态。
戴着黑框眼镜、黑黑壮壮的严龙40岁不到,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个国有单位工作。干了几年,严龙觉得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的日子太无聊,就辞职到了一家小型私企做高管,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自嘲说,公司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小老板”,“没有打工的这么干的”。每天晚上九十点回家,做饭吃饭,十一点看半个钟头电视,再看会儿书,大概一两点钟睡觉,早上八点钟起来,日复一日。
严龙的妻子是他原来单位的同事,虽然离他心目中的“女神”有点差距,但也是他欣赏的女强人类型。当年严龙也是花了心思感动了她,想着“好好过一辈子”。可是结婚以后,两人面对面的时间都不多,在家也很闷,没有话说。
妻子抱怨他太忙,希望严龙辞职回原单位。严龙拒绝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自尊心”。妻子工作出色,已经升职到单位高层,严龙说:“我这么傲,肯定不会回去的。回单位就是她管我了。”
严龙认为自己对妻子“很不错”了,“我从来打都没有打过她,骂也没有骂过。好多男的都打女的”。婚后岳父母来同住了五年,妻子有时抱怨他对老人不够好,他觉得他能忍下来已经不错了,“有哪个男人愿意跟长辈一起住?”严龙质问道。夫妻俩意见有分歧,他也“都不计较”,不和妻子争吵,自己干自己的,或者为了避免争吵就干脆瞒着妻子。在他看来,“吵架就要伤害对方,所以还是不要说的好”。
而家,对他而言并不是一个温暖的港湾。他说:“做我们这行竞争压力又大,企业的氛围又不好,这五六年我处在精神非常忧郁的状态。每天都在想,回到家也在想,在车上也在想,在公司也在想。回到家又乱七八糟,家里面也没有好吃的,没有宣泄的地方。”跟朋友一比,他的心理落差更大:
我最烦恼的时候,非常羡慕人家夫人什么的,根本没什么工作,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觉得很舒服。觉得自己的环境跟那个差得太远了。还有这种女强人,她自己也很累,她根本就不懂得怎么去安慰人家。那个时候我们去别人家,他那个太太就能跟他讲一些关心体贴的话,觉得很感动。
在公司干了五六年后,严龙突然想通了,不想这么拼命了,“我至少帮他(老板)赚了五六百万元,分到我手上也就是那么一万多美金”。半年之后,严龙跟一个小他十几岁的女孩好上了,他解释道:“我别的没有,我就是想有个人来理解我。”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对工作就没那么积极,有点怠工那样子。这半年轻松了以后,这精神也空了嘛,就更加想从家庭里得到什么东西……刚好也闹出一件什么事情来,更郁闷。就想找人谈,结果谈谈谈谈,就谈出事情来了。
那件让严龙“更郁闷”的事儿,是关于妻子的绯闻。妻子晚上总和别人短信聊天,一聊一个多小时,他听到原单位的人说妻子跟一个工地上的男人关系不错。严龙没有正面问过妻子,“这种事情怎么沟通?”他表现得无所谓,“我当时一点都不怀疑,我还有点大度。也不是大度,我心里有点纳闷,但是表面上我都没有表现出来”。但他心里却希望妻子有所改变,“风已经吹起来了。任何一个男的碰到这种情况都不会觉得舒服,他总觉得……不管是真是假,你总应该对我好一点”。
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严龙已然认为自己“被戴了绿帽子”,是“男人都不能接受的事情”。最让他想不通的是,跟妻子短信聊天的居然是一个“工人”。他愤愤地说:
我们知识分子啊,怎么能一天到晚跟那些工人嘻嘻哈哈,你有没有搞错?我当时心里非常自信,你说我们知识分子跟那些工人有什么共同语言,那些工人就是天天打麻将,天天不学习的人。……你成天不跟我说话,你还跟这种人说话,我觉得很奇怪,我讲一些话你都不帮我,不附和我一下,不管我是对还是错。
严龙和妻子都上过大学,在市场大潮中抓住了机遇,成为新兴的中产阶层的一分子。夫妻双方都有很强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自愿自觉地进入加班大军中。家对他们而言是获取情感慰藉、关心和温暖的地方,他们渴望得到照顾,听到关心体贴的话,而他们都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给予对方关照、说出关心体贴的话,把家打造成“有爱”的地方。他们都开始向外寻求情感慰藉,满足精神需求,最终演变成一场家庭危机。
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对美国双职工家庭的经典研究发现,夫妻对于婚姻角色存在三种不同的性别观念:传统型、平等型和过渡型。传统型认同丈夫作为一家之主、挣钱养家,而妻子的身份则围绕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即便她事实上外出工作);平等型主张夫妻双方齐头并进、权力均分;过渡型则是指处于传统型和平等型中间的状态,比如一个过渡型的丈夫会完全支持妻子在外工作,但同时期待她在家务事上也能挑起大梁。
严龙是一位典型的过渡型的丈夫。他支持妻子的事业,妻子的事业心和工作能力甚至成为吸引他的重要方面,但是他认为照顾家庭是妻子的责任。严龙有时在家里也做饭,但他觉得这是妻子欠他的,“毕竟我们这个年代,事业心都很强,一般都不肯为一个女的做家务”。而他可以顺理成章地指责妻子回家“家里也不管”、“小孩也不管”,并为此感到失落和不满。家庭照料不仅是料理家务,还包括照顾家人情绪、满足情感和精神需求。严龙的情感处理方式是忍耐负面情绪,避免伤害,并将此作为对妻子的“善待”,而期待妻子说体贴的话,安慰和理解自己。换言之,丈夫参与共建一个“安全”的家,而营造一个“温暖”的家的主力则是妻子。严龙的参照对象是遵循传统性别分工的家庭,那些顾家的妻子对养家的丈夫体贴入微,由此,他的失落和不满也显得合情合理。
小徐小学毕业就出来混,用他自己的话说,“不爱读书,爱玩”,只能“找门路”做生意。他父亲和爷爷都是做生意的,他自嘲说:“要说大钱没有,小钱不缺,可能从小我就玩惯了。”他认识的人也大多没念过几年书,早早就出来做生意了。潮汕人有做生意的传统,信奉“生意小小也可以发家”,小徐颇为羡慕地提到自己的邻居,“一个字都不认识,现在都发大财”。
小徐20岁的时候家里托媒人给说了个对象,本地姑娘,母亲过世了,哥哥嫂嫂在香港做生意。其实小徐当时他自己谈着一个女朋友,外地的,家里不同意,“在我们那儿就没什么人娶外地女的,”小徐说,“我糊里糊涂的,听我老爸老妈这么说了,也许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喜欢(那个女朋友)。”在父母的安排下,他和老婆见了两面就定了亲,几个月后就结婚了。
在小徐眼里,老婆“头脑比较简单”,两人“沟通不来”。最让他耿耿于怀的是老婆不“管”自己,不闻不问,“我老婆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样想。出来外面,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她也不会说什么,从来没有说要我回去啊”。一次在老家他和朋友通宵打麻将,“四个人三个老婆都来找了,就我老婆没找,”他愤愤地说,“气死我了,就像我没老婆一样。”
婚后那几年小徐在老家做假烟生意,家里雇了60个工人,每个月能赚好几万元,最好的时候甚至有几十万元。钱赚得快,花得也快。小徐出手阔绰,吃饭、泡吧、唱歌、打麻将,一个晚上几千块也是常有的事儿。他在足浴店认识了一个年轻漂亮的湖南姑娘,开始疯狂地追求她,每天带着朋友去她工作的足浴店消费,晚上带着她去卡拉OK厅,吃宵夜,日复一日。小徐感慨道:“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喜欢一个人,我什么都愿意付出。”
两人在一起一年多,小徐一直很舍得花钱,日常开销都包了,她想买什么做什么也都痛快答应。小徐说:“怎么都开心了。反正这个钱了,都是身外之物,花了又赚回来了。”也正是那个时候,六合彩在当地流行起来。小徐一下子玩上了瘾,三个月输掉了几十万元,变卖了家里的车和值钱的东西,还欠了十几万元的债。姑娘这个时候跟小徐提出了分手。“我刚六合彩一输,她就说分手,”小徐略带伤感地说,“我给钱她花啊,吃啊玩啊,她都听我的,到了没了,她说要分手,你说人就是这么现实。”
在老家待不下去了,小徐来到了广州,靠做生意的弟弟接济继续“玩”。小徐不愿意打工,他自嘲“我一没技术,二没文化,打什么工呢”,“一个月1000、2000块”,挣不到钱,“没什么意思”,也多少有点“没面子”。他想做生意,一来没本钱,二来也找不到好的门路,就这么混了好几年,没钱了给弟弟打个电话,弟弟派人送点钱过来。前年老乡给他介绍了看工地的活儿,不用出苦力,清闲也体面,一个月2000多块,小徐干了一年多,工程结束了,他也没再找新活儿。
虽然没什么钱,却碰上了几个死心塌地想跟他好的姑娘。小徐笑笑说:“怪,我也是觉得怪。老是觉得我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一般你跟人家交往,你要知道人家图你什么,我什么都没有,也许人家就是图一个开心。(你跟那些女孩子在一起都很开心吗?)反正我跟那些女孩子,都没有吵过架。”
最让小徐过意不去的是一个开便利店的湖南姑娘,小徐常去她的店里,一来二去好上了。小徐一开始瞒着对方说没结婚,“我那个时候也没想什么,毕竟一个男人在外面找个女人是正常的嘛,是不是?我就想找个女人。我跟她住在一起两年多。她一直觉得我是会跟她结婚的。”得知他已经结婚后,对方很生气,但还指望他离婚。小徐回忆道:“她说,我跟你去你家里,跟你老婆谈判好不好?只要你老婆同意,多少钱我都愿意给。我都不知道她心里怎么想的。”
“长那么大,我就骗过这么一个女人,”小徐有点不好意思,“她也感觉不出来,如果有老婆的,怎么会没有老婆打电话过来?除非有事情,不然她(老婆)不会打电话给我,一年不会超过三次的。像去年,没打过一次电话。”说到这里,小徐又一次感慨自己婚姻不幸:“真的,我都哭过好几次,我想不到我娶了这样的老婆啊。要是老婆对我好,我也不会在外面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