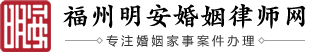“离婚冷静期”干涉婚姻自由了么?
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的民法典已经出台,其中“第五编”、“第六编”修改完善了若干家庭关系、婚姻制度的法律规定。其中设置了三十日的“离婚冷静期”,被不少网友点评为“限制了解除婚姻的自由”、“法律给脱离婚姻苦海挖的坑”、“降低离婚率的强制手段”。“冷静期”真的是公共利益对私人自由的限制吗?爱情消散后,法律强迫我们延续婚姻了吗?要恰当理解这个制度背后的价值理念,我们可以从区分“爱情”与“婚姻”的社会属性开始。
爱情是瞬时性的感性体验 ,它是突破社会理性的“绝对自由”
爱情的核心要素之一是“非理性”的“激情”。“激情”象征着一种私人世界,它正因为突破理性的限制而存在。在浪漫主义的爱情观念中,爱情甚至作为一种精神或心理上的“病态”存在。它被描述成“疯狂”、“神秘”、“奇迹”和“不可论证”。由于它在理性精神勉强的疲软无力,很多时候爱情要突破社会限制,可社会某些情况下容忍这种“疯狂”,某些情况下又惩罚这种疯狂。因此,浪漫主义爱情文学中,“激情”往往与社会标签、自我身份的毁灭相联结,爱情与恋爱者进行斗争,始终站在社会认同的对立面,在勇敢与懦弱、疯狂与不安、愤怒与尊敬、自我建构和自我毁灭中强化,形成了丰富的文学素材。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经典汇集了大量对于求爱者苦涩心理体验的描写“一旦某人将他的心给了一位美人,他就只能一心一意的想着讨她欢心,除了她的意志而没有别的意志;不管他原来是什么脾性,他得强迫自己服从他的感情。必须要研究她的所有想法,观察她的所有举动,以便为之雀跃欢呼,要全然忘记自己,以便只能想起她,向她的美貌表示敬意。”爱情首先引起了内在的“自我战争”,中世纪贵族男性的“英雄主义”形象被突发的激情所解构,他们试图用“英雄般的钢铁意志”抑制爱所带来的软弱,却最终臣服于爱神的箭矢,绝望地寻求所爱者的回应,在意中人的面前屈膝。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爱情觉醒后突破人格限定的角色多由女性来塑造,无论女主角的阶级身份是大家闺秀,抑或是青楼女子,都在自我醒觉的道路上拥有了高度风格化的心灵美德。比如,《西厢记》里的莺莺从温柔、端庄但麻木的单薄形象蜕变成果敢、活泼,为爱用尽手段心机、但又一心一意向往单纯婚姻的丰满形象;又如,《警世通言》里的杜十娘“错把禽兽当知己,误把砒霜当蜜糖”,从误落风尘到为爱赴死,前后的身份反差使她的刚强、忠贞得到十足的呈现。
爱情里的非理性,始于对人物“完美特性”的追求,比如美貌、才情、内在美德、智慧等等,但最终其必然超越了可被外界观察的人物特征,回归到恋爱者私人体验的“完美”中。“情人眼里出西施”,美丽的双眸经常性地成为爱情的开端,但只有亲历者不知所以然的精神体验、以自我视角对对方的观察、描述、美化,才能使笼罩对方完美形象的“月晕”持续散发光芒,一旦一方停止了描述,光环即被打破:当我看你如同世人看你一样,爱情的火焰就无法继续制造梦想。因此总不缺人在抱怨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以为我娶的是位仙女,后来发现我娶回了一坨牛粪;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只能依靠做梦”。由此,爱情的非理性表现为对“自我”理性秩序的突破,以及对“他者”非理性的描述。
爱情的核心要素之二是“欲望”。“欲望”属于理性范畴吗?从理性的角度来说,欲望包装了人类追求的理想爱情,以对爱的排他性“私有”成为爱的意义要素,实质却服务于人类的繁衍任务。显然,这种庸常化的描述并不被沐浴在爱河里的情侣们所接受。因此,“欲望”本身没有理性或非理性的区分,但当“欲望”被框定在爱情的语境中,它又必然与理性形成了对抗。包法利夫人以为非理性的欲望可以满足她在婚姻中求而不得的爱,“结婚以前,自以为就有了爱情。可是,婚后却不见爱情生出的幸福。欢愉、激情、陶醉,这些当初在书本中读来的美好字眼,生活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她渴望答案,而当欲望再一次遁入新的关系秩序中,答案却令她大失所望:“他们太相熟了,颠鸾倒凤,也不再是一种惊喜万分的事。她腻味他,正如他厌倦他,她发现了这种关系的平淡无奇,但没有作分离的决定的勇气,但她坚持给他写信,因为女子理应当与自己的情人通信”。可见,爱情中的“欲望”并不排斥非道德性的性吸引力,相反“欲望”在爱情的语言系统中超越了世俗化道德,上升到突破文化、法律规范的“灵魂指引”。爱情本身并不排斥桃色事件,尤其是在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解放的时代,艳遇总是被描述成诗意且奇妙的。
婚姻是恒久性的制度安排,它是遵从社会理性的“相对自由”
问题随之而来,作为浪漫主义爱情要素的“激情”和“欲望”均不属于理性范畴。那么象征着私人意志绝对自由的爱情就属于“法外之地”,然而作为爱情最终归宿,且为爱情延续提供身份保障的婚姻,本质是理性还是非理性呢?它属于“法管领域”还是“法外之地”呢?
现代社会的婚姻关系,为爱情提供了一种制度性解决方案。无论是黑尔格所说的“婚姻是精神统一的伦理关系”,还是社会主义婚姻观念倡导的“当事人间的互相爱慕应当高于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实际上都涵括了一个基本题设,即婚姻是建立在道德、理性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不仅只负责提供当事人间爱的心灵体验,还负责提供某些社会功能。社会理性承担着一种“普遍管辖权”,以制约人们以追求不稳定的爱情为名,过于自我地玩弄着“不负责任的把戏”,造成社会伦理秩序的风险。爱情如果走入婚姻,就需要放弃一些危险的、过分狂热的激情,服从于婚姻的社会调节功能。毕竟,像少年维特那样陷于爱情“无意义的茫然”,以吞枪自尽来表达爱,并不是社会所欲的爱情导向。当然,婚姻的稳定性并不意味着现代法律不包容解除婚姻的自由,或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迫使不幸婚姻存续。这样的理解显然混淆了法律对于婚姻的功能,实际上,法律设置婚姻的解除条件,基本出发点多集中于两个:第一是确认婚姻解除基于双方理性的合意;第二是保护弱势方在婚姻解除后不至遭受生活的困境。法律仅对婚姻提供有限的保障作用。
20世纪前半叶的立法进路,普遍将强调婚姻的身份关系属性,由于婚姻与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的密切关联,国家被视为“有责任提供婚姻权利、义务的制度性规范”。因此,公权力对婚姻事务的介入较多,婚姻法中体现法律统治的典型制度包括:同居义务、抚养义务、过错离婚等等。一些法律明文规定了“实质损害婚姻”的离婚理由,并且将解除婚姻的诉请权交给无过错方,为他不幸的婚姻提供“解救措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婚姻中的经济依存关系大大减少,人们对婚姻更多投注了情感、心理上的期待,降低了对财产共享的期待,婚姻中的个人意愿要素得到空前强化。
那么法律如何又调整婚姻制度,以适应这一变化?晚近的立法多明文承认夫妻双方有权依法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约定,包括家庭生活方式、家庭事务管理、财产的变更、终止及分割、子女的抚养等等,法律不阻止双方婚前拟定各种类的“协议”,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双方可以约定夫妻姓氏。“约定优先于法定”的原则本身就象征着婚姻制度趋向私人意思自治的潮流。在“契约婚姻”观念下,法律制度倾向于道德中立,它仅提供缔结婚姻的法律要件,由夫妻双方自行填充大部分婚内权利、义务的实质内容,特别是在财产关系的处理上保留高度自治空间。但即使在完全道德自由的背景下,婚前协议和离婚救济仍由法律进行必要限制,这其中当然存在着理性基础。第一,任何类型的契约都不能严重违反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婚姻协议也必须遵守这个底线;第二,无论当事人的人品好坏,都要遵守基本的契约精神,如果违背了契约实质义务,侵害了他人的权利,还可以毫无代价的“单方解约”,在一切场景下都会“显失公平”。
设置离婚“冷静期”,并非由我国民法典所首创。我们当然可以批判国家为了降低离婚率,不惜牺牲了即时结束婚姻的“自由”,但以笔者的角度来看,“冷静期”恰恰提供了对婚姻双方自由的绝佳保护,因为在很多情况下,非理性的结束婚姻为夫妻双方都施加了额外的成本。在“激情”、“欲望”都呈现出它们与婚姻系统的不可弥合之处后,人们开始重新寻找亲密关系的质性基础。一个社会私人的个体化程度越高,寻找到符合其一切预期之配偶的概率就必然越低。因此,配偶选择的论证不再由“我找到上帝为我设计的完全相容的个体”开启,而是趋向由尊重个体差异、从沟通的努力中探寻理解所开启。如哲人所言,“人们在婚姻中寻找的,不是拔高到非实在性的理想世界,更不是炽热情感的持久证明,而是在所有重要事情上相互理解和共同行动的基础。”
无数心理学、社会学著作论证了婚姻中伴侣双方“友谊基础”的重要性,恋人们无休止地聊天,并不在于能够从对方身上得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而是得到对自我的回应。一旦迈入婚姻的围城,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它不可能被看成纯粹的契约。首先,婚姻受益于长期的承诺,提供最可信赖的终身合作关系。普通合同当事双方的权利义务大多是“对抗性”的,而多数情况下配偶双方基于“合作性”来实现共同利益;其次,任何协议都无法穷尽婚姻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契约权利是可列举、可穷尽、可量化的,而婚姻生活是不可穷尽、不可量化的。几乎不可能有人能在结婚之前预见到婚姻进程中的偶发事件,夫妻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物质的、非物质的交换,意见的交换、财物的交换、性的交换、抚育子女责任的交换、情感的交换、劳动的交换等等,它是一个变动的、持续进行的发展过程,不是简单的合同条款,双方无法要求交换的权利是绝对平等的。也正是因为婚姻的“权利规则”只有当事人在相处过程中才能达成,并没有普适性正确标准,亲密关系才特别容易培育失望和冲突,对权利分配的不满、具体行动的差异、价值评估的标准、“对”或“错”的评判,经常使两个亲密无间的人突然间产生了对立而放弃了白头终老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看,婚姻“冷静期”意在为处在对抗情绪中的夫妻提供了一定的调适余地,让双方尽量理性地考虑长期“合作”的基础是否依然存在。婚姻既是一种私人事务,又是一种社会关系。任何长期的亲密关系里,失望与无力感都必然存在。能否不断找到新的共识,要取决于两个人是否在关系中不断调整预期、抱着开放性学习的心态审视冲突。法律规定的30天冷静期,既不会消除真实的情感裂痕,也不能阻止一个坚定的人奔向新的幸福,人们大可不必恐慌法律剥夺了自己的婚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