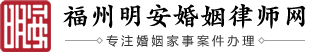根据科学研究院的平均统计,在我国,同性恋者总人数超过70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5%。作为性少数群体,他们对婚姻、家庭、事业有着和普通大众同样的诉求。但是我国大陆法律对于同性恋的权利保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除了法律制度的缺失,他们还要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
作为维护性少数群体权益的专业律师,上海兰迪律师事务所的任丹律师和常俊兰律师认为,一个包容、多元的社会应当接纳性少数群体的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谈,每个人都可以也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作为法律人,她们看到了这一群体的诉求,也决心以法律为武器为他们寻求公平……
权益难保障
任丹律师和常俊兰律师介绍,性少数群体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法律权利问题主要包括:如何缔结婚姻、财产分割问题、职场平等权问题、孩子抚养权问题等。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面对两座大山,一是无法(针对这一全体的立法)可依,二是举证困难。
“同性恋如何缔结婚姻,目前大陆地区没有法律规定,我们暂且抛开不谈。”
至于其他问题,比如财产分割,双方同居多年,财产已经发生了混同。如果按照婚姻法,夫妻双方离婚,适用共同财产制,只要划清共同财产,就可以平均分割。
“但是同性伴侣更类似男女同居,可以参照异性同居财产分割,他们需要证明什么时候开始同居、同居期间财产是否发生混同,如果这些都能够证明清楚,那么财产的共同部分也可以平均分割,但是这个过程中,存在举证难的问题。”
常俊兰律师补充道:“举证难的问题也存在于职场平等权问题中,性少数群体因为性取向遭遇职业歧视的不在少数,但大都很隐蔽,如何搜集证据证明公司之所以开除你是因为你的性取向?”
举证的重重难度,都对律师的功底以及对案件的把控程度有很高的要求。
为同性伴侣监护权开窗
一对六七十岁的女同伴侣已经交往很久,其中一人住院面临手术,另一人却因在法律上不是合法配偶而不能签手术同意书。这是蔡依林的《不一样又怎样》的MV中讲述的故事,据说改编自一段真人真事。
“这确实是很多同性伴侣面临的困境。”任丹律师表示,随着“意定监护制度”的引入,这个问题发生了转变。
事实上,我国在2012年修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之前,一直使用的是“法定监护”,即由法律直接规定监护人范围和顺序的监护。而成年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法定监护人指的是:(1)配偶 (2)父母 (3)其他近亲属(4)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直到修正《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我国立法正式引入意定监护。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的监护人。老年人未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后该法在2015年、2018年两次修正中均保留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而我国2017年《民法总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协商确定的监护人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履行监护职责。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继续保留了这条规定。
《民法总则》增设了适用于全体成年人的意定监护规则,并赋予其较之法定监护的优先效力。这是对我国传统成年监护规则的重大变革,对于推动我国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任丹律师告诉记者,意定监护虽然不是针对性少数群体设定的,但它被视作目前中国同性恋关系的“最优解”。
根据这项规定,监护人的范围可以是任何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其中并未把同性伴侣、同性恋人排除在外。因此,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同性恋者,完全可以依据该规定,在其具有意识和民事行为能力时,将其同性恋人或同性伴侣选任为监护人,将自己的人身照顾和财产管理等事宜委托给该监护人,待自己丧失意识能力后,由监护人按照其的意愿处理生活照管、医疗救治、财产管理、维权诉讼和死亡丧葬等监护事宜。
那么同性伴侣之间如何办理意定监护呢?
一般来说,办理意定监护的委托方和受托方需要签署《委托监护合同》。在整个意定监护制度中,《委托监护合同》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合同内容贯穿了监护人选任、监护事项分配,监护关系设立、监护责任承担、监护关系终止等各个环节,对于监护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起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监护合同与《民法典》中规定的委托合同类似。因此,监护合同的成立、生效、解除或终止的基础规则,均可以参考《民法典》适用民法典委托合同一章的相关规定。
由于监护合同订立之时,被监护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监护合同在法律性质上应属于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只有当监护原因发生时,监护合同才生效。
同性权利纷争热点
日前,厦门湖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全国首起女同性恋人抚养权纠纷案件。“基因母亲”与“分娩母亲”谁才是孩子法律意义上的母亲?最后,法院判决认定“基因母亲”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母亲,分娩者为生母。那么法院判决的依据是什么呢?
在此案中,A、B是一对同性恋人,为了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双方购买了精子,并通过生殖辅助技术将A的卵子与购买的精子培育成受精卵后,移入B的子宫,由B孕育分娩。A、B的行为其实可以参照代孕,虽然这一行为不为我国法律所容许,但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指导性案例供参考。
记者查阅发现,在最高院公布的上海一中院关于代孕的指导性案例中,法院认为“母子关系的确立更多在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和分娩艰辛所带来的情感联系,在于母亲对孩子在精力、心血、感情上的巨大投入和无形付出,单纯以生物学上的基因来认定母子关系,将缺乏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支撑”。因此在判决中采纳“分娩者为母”的原则来认定母子关系。
任丹律师和常俊兰律师认为厦门一案的当事人双方是基于同性伴侣关系而进行的代孕,目的是为了共同组建家庭,在这样的前提下,仅依据“分娩者为母”原则否认卵子提供者生母身份,并没有考虑到同性伴侣家庭的特殊性和客观需求,双方分手后,只有一方获得子女的监护权,另一半对孩子甚至没有探视权。
“无论当前法律制度对同性婚姻、代孕的观点为何,同性伴侣家庭的子女合法权益都应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在司法裁判中,也应该参照异性婚姻关于子女抚养、探视、监护的规定,让同性家庭的成员也享有爱与被爱的权利,这样才能真正的保护同性伴侣家庭子女的最大利益。”
性少数群体维权难题
职场上,更看重的是个人的工作能力,但是往往也会出现因性别、肤色、民族、性取向等多种原因遭到歧视的现象。据统计,进入职场工作的性少数群体中,有超过八成的工作者在工作中遭遇歧视或者感受到歧视。
在我国当下的社会大多数对性少数群体持不理解甚至不友好态度的环境下,他们大多数会选择小心隐瞒个人性取向,融入大环境。如果不小心暴露了真实性取向,往往就是被公司以其他理由解除劳动关系,比如业绩不佳,也可能因为公司效益不好需要裁员。那么,这种间接又隐蔽的因性取向而造成的就业歧视,他们该如何举证证明呢?又该如何维权呢?
任丹律师说:“尽管我们都知道‘变相解雇’本身就是赤裸裸的歧视,但中国的《劳动法》中没有就‘就业歧视包括性倾向歧视’‘不得歧视性少数群体’作出说明,再加上举证难的困境,几乎难以维权。此外,如果性少数群体执意以就业歧视为由向公司诉求就业权益,反而会让自己深陷舆论、社会歧视的漩涡,这也导致性少数群体就业权益的探讨处于失声的状态。”
性少数群体因就业歧视寻求法律帮助难如登天,但却并不是一条绝路。
法律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说明,但是此前“当当网公司技术部产品总监高某某因做变性手术被公司按旷工解雇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判决结果,传递了倡导社会以更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性少数群体的价值导向。
记者在这起案件的判决书中看到,终审法院认为:现代社会呈现出愈加丰富多元的趋势,我们总是发现身边出现很多新鲜事,我们又会学着逐渐的去接纳这些新鲜事,除非它威胁到了他人、集体、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也许正是我们对很多新鲜事的包容,才奠定了文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长足进步。我们习惯于按照我们对于生物性别的认识去理解社会,但仍然会有一些人要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来表达他们的性别身份,对于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表达,往往需要我们重新去审视和认识,这种重新审视和认识或许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确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包容,我们也确有必要逐渐转变我们的态度。因为只有我们容忍多元化的生存方式,才能拥有更加丰富的文化观念,才能为法治社会奠定宽容的文化基础,这或许就是有学者指出“社会宽容乃法治之福”的逻辑。我们尊重和保护变性人的人格、尊严及其正当权利,是基于我们对于公民的尊严和权利的珍视,而非我们对于变性进行倡导和推广。
这一判例也让任丹和常俊兰律师,以及诸多为性少数群体权益奋斗的法律人们,看到了法律逐步接纳性少数群体的迹象,社会观念日益开放的变化。
社会发展的趋向是多元、平等的,随着社会的开放程度加深,越来越多的人敢于正视、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同性恋已经从一个私人问题发展成为公共问题,他们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这在我国目前几乎空白的保障同性恋权益法律背景下,仍然道阻且长。